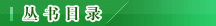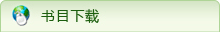|
踏 遍 青 山 情 未 老 |
|
2007年01月19日 |
|
我们处于一个散文的时代。近十多年,随着经济的勃兴,文学环境的宽松,各种媒体的迅猛发展,散文创作碰上难得的繁荣机遇。与同期小说、诗歌等传统文体式微相比,散文的“梅开二度”显得格外耀眼。 “文化散文”、“学者散文”、“休闲散文”、“快餐散文”等等,如走马灯一般,令人目不暇接。 然而,在散文多样化与多元化背后,也并非就是众“声”平等、争奇斗妍的。曾几何时,意蕴空洞的“诗人”散文和沉迷于都市生活情态的“小女人”散文,大行其道。梁实秋、周作人等闲适的小品文,也长期担任领衔主演的角色。而另一方面,但凡和革命、英雄沾上边的散文,则被打入“宏大叙事”、“革命话语”的另册。散文批评也缺乏那种鞭辟入里、洞察入微的卓见之作。这个时候,梁衡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异军突起,把“一堆被狭隘的党派意识腌烂了的咸菜”重新翻拣出来,直言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,把山川风物和历史大事联系一块,从这些“大事”中体会领袖、伟人、革命者、英雄、典型人物的“大情”,把这些“大情”升华又为人生的“大理”,以“掣鲸碧海”之手笔,补“翡翠兰苕”之不足,可谓大气磅礴、洞天别开,引人深思。 散文一旦触及“主旋律”,处理得不好是容易遭人嫌弃的。现实生活中,硬生生地把“真典型”写成“假典型”的文字,屡见不鲜。因此,若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,又要充满诗情画意,实属不易。这里的要诀,就是要把伟人与凡人之间被“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”。而做到如此,关键就是要遵循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——“艺术源于生活”,同时,掌握以情动人的散文技巧。这些,梁衡都出色地实现了。 学界目前在反思“纯文学”,认为80年代后期对审美的过度强调,部分导致了90年代文学(特别是小说)介入现实的无能。90年代散文热的兴起,从旁证明了远离现实生活、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小说失宠的症结。毫无疑问,写散文没有广泛的阅历,没有生活积累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有优秀散文作品,在创作经验上有一共同点,那就是作者的文化和生活积累都比较厚实。我们对照一下同时期的小说创作,就不难发现,小说创作中有关“代”的经验陈述特别多,少年得志,一夜成名者不乏其人。但散文作者壮年和老年人居多,大都是笔耕数十载,个人修养也达到相当高的境地。梁衡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,便是一个突出的、令人别有一番惊喜的例子。 梁衡走的是一条“无中求有”的新路。他要把伟人成为伟人“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”,要“沟通情理,有血有肉,让读者可亲可信”。而要做到这一点,若无“踏遍青山”的阅历,是写不出小到山西某偏僻小县的一起冤案(《桑氏老人》)、植树老人(《青山不老》)、乡村女教师(《热炕》),大到有关马克思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胡志明的文章的。梁衡的散文,乍看起来有些类似“学者散文”、“文化散文”,但细看又与它们不同。他不但写“文人”、“佳人”,还写“伟人”、革命者;不但写古代的事,还写近现代的事。这些对改变人类和民族命运人物的诚挚赞颂,对“红色历史”的深情沉思,是一些喜欢掉书袋、贵古贱今的文化人所不为和不能为的。 看来,梁衡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作一个“学者”。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劳动者,既是官又是民,是多重身份的统一。他写领袖人物不媚俗,写革命事件不矫情。他会“顺藤摸瓜”地“去找那些碧绿的叶子和芬芳的花朵”。这大概跟他的切身经历、切身体验和立意高远不无关系。俗话说得好: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他写瞿秋白,构思六载,三访其纪念馆,是深切的感情体会在催他这么写,而不是“领导”或“市场”要他这么写。他写红色典型,也没有把它当成歌功颂德的工具,而是从分析对象的人格、作风、方法入手,把他们看作健旺的民族精神的化身。梁衡状写伟人,很能抓神,既平实可信,有入木三分。如写瞿秋白,没有一味地悲叹其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,而是通过与同时代的梁实秋、陈望道作对比,说明一个本该在文学艺术界成为泰斗的学者,为了民族大义,自动放弃展才之机,却又英年早逝。这样,一个革命者悲壮的意味就凸现了出来。 伟人、典型人物是一个民族的标本。通过解剖这些人物,我们“对照现在发生的事情,新的矛盾,新的课题”,会“发现许多事情在他们那里早已解决,或者深受启发,成了一把打开现实之锁的金钥匙”。这是作者通过散文对现实问题的回应。我们这个时代,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人的价值和浩然正气的呼唤。作者面对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说话,面对真实的内心说话,因此,十分感染人,也特别能征服人。有作家说过,“好的散文,有读史之慨”。梁衡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,成了中国革命史的灵魂聚焦和鲜活侧面。这是那些不关注内心而专写内分泌的写手,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。 散文要写真实的生活。真情、真话、真感觉,这是散文创作的不二法门。新时期初期,有些散文受到一些诟病,原因多在于抒情太过,好篇末点题,几成套路。但这不意味着散文不需要情感。如果说那时的问题大多是由于时代局限产生的技术问题,那么,现在到处泛滥的煽情文字,动不动眼泪与哲理齐飞,哭泣与遐思共舞,就让人有点疲惫与肉麻了。近两年来,关于“余秋雨现象”的争论,一个关键问题,就是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。这在事实上是比某些篇章中的“硬伤”更为致命的。审美经验告诉我们,质朴的东西比做作的东西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有人讲:“凡是渲染、夸饰、做作、有意要去打动人,感染人,煽动读者情绪或兴致的,一概就没有好的”。(止庵:《六丑笔记》)似乎说得有点绝对,但确不无道理。 散文创作的主体性强,客观现象与主体意识往往融合,即使那些裸露的文本,其背后也可能隐含着某种私秘性、个体性和复杂性。这是散文的魅力所在。鉴于此,梁衡摒弃了90年代僵硬的抒情模式,抒情而不滥情,寓情于史,凝重肃穆,审美之中带有理性思考,所以,读来既风行水上、自然成文,有透射智慧、升华情操。 当然,写散文仅有主观的真诚是不够的,让读者接受,还需要多方面的技巧。梁衡写伟人之所以常写常新,就在于他认识到普通群众对伟人的了解往往重结果:丰功伟绩、理论言说,但常常忽视伟人的前史,即他们功成名就之前的挣扎和艰难漫长的过程。在这个创作思想引领下,他找到了瞿秋白故居、尤其是门前那座已成过去的“觅渡”桥,找到毛泽东写《论持久战》时的延安窑洞,找到中国共产党指挥国共大决战的最后一个乡村战略指挥部——西柏坡,还有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。他甚至远渡重洋,在日本找到周恩来游历过的岚山及岚山诗碑,在德国特里尔找到马克思出生的房子。伟人的思想和业绩,是一棵大树。他要找的正是这棵树的根、它的年轮和生长点。而这些,是最能给读者带来震撼的精神与审美的亮点。他的思辨,他的叩问,在他的文字里都得到了舒卷自如的挥洒空间。 我喜欢梁衡的散文。读他的散文,能感受到一种成熟的朝气,一种崭新的律动。他是踏遍青山情未老的歌者,他的散文是培植健康人生观的佳酿。这也许就是革命精魂的作用罢。革命者是不朽的。歌颂革命的优秀散文,我相信,也是不朽的。因为。它们与历史同在。 |
上一篇:再现真实的马克思 |